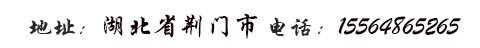食记溧水的野菜,那些好吃的ldqu
|
清朝有个人叫袁枚,写了一本《随园食单》,据说是厨师必读经典。 我闲来没事看了两个版本,发现书里有许多菜都很熟悉。最巧的是看到他有一节写,记录了在溧水当代理县令时在“叶比部”家喝到的美味。 “其色黑,其味甘鲜,口不能言其妙。据云溧水风俗,生一女必造酒一坛,以青精饭为之。俟嫁此女才饮此酒。以故极早亦须十五六年。打瓮时只剩半坛,质能胶口,香闻室外。” 叶比部是谁呢?清朝名将叶名琛的爷爷,叶名琛也是溧水籍人。他爷爷招待袁县令,拿出了一坛好酒,乌亮亮的,说这是溧水人嫁女儿用的。女儿出生时,用乌饭酿酒,过了十五六年开坛喝掉。袁枚说自己不大喝酒,但是那一口喝下去,就不停了。 看完我想了想,啊,乌饭酒,我都没喝过。不过我结婚的那天恰逢四月初八,吃了一口乌饭……但看到清朝人写的东西,我不禁对我吃了几十年的食物感到好奇了。 也许过了年,我现在吃的以后也没人吃了呢? 于是就写写我家乡的食物吧,仅供娱乐。 溧水地属江南,环山抱水,丘陵起伏。说起吃的,我们光水里游的就能分江鲜、湖鲜、河鲜,山上的奇珍异宝更是丰富。 以前在外地读书工作,被人问起家乡有什么好吃的时,脑子里总是嗡嗡的。 “好吃的?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啊。” 人们说起南京就会说鸭子,盐水鸭、桂花鸭、板鸭……噢没错,我们这里鸭子确实好吃。不过鸡也好吃,鹅也好吃,鸟都好吃,好吃的又绝不仅限鸭子。 如果你去农家走一走,除了路经大片山林和田,再细看各家门口的院子,绝不留一点空地。种点东西,瓜果时蔬,四季丰腴,就是我们平常人家的生活。 溧水的菜,不像某种菜系讲究烹调的刀法或调料,我们说起吃的,首先就要求食材好到 。野鸡野鸭野山珍,野虾野鱼野生鳖——野味得其时,时令就是世间最 的烹饪大师。 而我们所擅长的,恰恰就是不入主流“不上台面”的东西,就是那些遍布山川的野味。 说到野东西,时令的野菜最与人亲近。 春天是野菜最蓬勃的时候。天气一暖和,溧水人就耐不住性子要去地里了。不管城里的还是乡下的,大家都十分默契,拎着个菜篮子。去树林间、花园后,蹲在小路边,纷纷弯腰去捡宝。 大人们像极了小孩,天真地要钻到草丛里。我听一个溧水的女孩说,她妈妈每周末都要去捡野菜,看到一堆草的时候两只眼睛都发亮,那样子可爱极了。 溧水人家的餐桌上顿顿都少不了野菜,从春到夏,“几头一脑”——香椿头、荠菜头、马兰头、枸杞头、豌豆头、苜蓿头、菊花脑,挨个吃到夏季。 ▲野生荠菜包的饺子 荠菜头是最寻常的。一般人用来包饺子,还有的包包子。 有句民谚叫“三月三,荠菜花煮鸡蛋”,城里我是不知道的,但在溧水南边的村子,用荠菜花煮鸡蛋倒是很常见。 石山下“毛毛雨”家有道菜,荠菜花汤煮鹌鹑蛋。把鸡蛋改成了小鹌鹑蛋,煮的时候,用生荠菜花和生鹌鹑蛋放在一起,煮一会儿拿出来,凉一会儿再继续煮。蛋壳敲敲碎,荠菜花的香味可以渗进蛋里。如此三煮三晾,荠菜的味道才会进到蛋里。 ▲荠菜花汤煮鹌鹑蛋 野菜配鸡蛋,天经地义。不光是荠菜,香椿头、菊花脑也很配鸡蛋。 香椿头在雨后冒出来,“雨前椿头嫩无丝,雨后椿头生木枝”,谷雨之前是吃香椿的季节。 打几个鸡蛋,摊饼,或简单炒一下,要点是用菜籽油——而不是什么色拉油、花生油。 油菜的油,配香椿的头,把鸡蛋炒老一点、暗一点,才配上香椿的威武,它的涩味才从油里冒出来——“一箸入口,三春不忘”。 ▲香椿头炒鸡蛋 最配鸡蛋汤的是菊花脑,一般到初夏时节上了(也就是现在)。用句时髦话说,菊花脑带着“性冷淡”的味道,清香、清香、清香至极。 它是属于懒人的菜,天气热了没胃口,就从院子里的一畦菜地上摘一把菊花脑叶,在锅里滴两滴菜油,打个蛋在沸水里滚一下——同样的配置,又是一番好滋味。苦夏时候,最需要苦兮兮的冷淡滋味。 ▲菊花脑长得就很冷淡 在凉拌吃法里,最神的当属马兰头,几乎无其他野菜可以与之匹敌。 它从料峭春寒时出来,也相应的 凉丝丝的气息。 马兰头配香干,配之前要无情地把它剁碎。用香油拌一拌,好油之人可以再加点花生米——那种好看的点点碎绿,和整个冬季大鱼大肉后的清凉滋味,最能唤醒人对山野的记忆。 ▲马兰头拌香干 说了这么多“头”和“脑”,说点正儿八经没那么野的。 苋菜,与蚕豆、茭白称初夏江南三鲜。孩提时我总把马齿苋和苋菜弄混淆,溧水话里叫“汗菜”,我还真以为吃了“汗菜”会出汗。其实,马齿苋和苋菜截然不同,苋菜更像一般野菜的做法,清炒最赞;而马齿苋深谙世事,晒得干瘪了做红烧肉 吃。 做野菜不需要添加多余的味道。郑板桥最喜欢夏季暴雨后乡间一畦苋菜:“白菜青盐苋子饭,瓦壶天水菊花茶。”张爱玲吃苋菜,说:“炒苋菜没蒜,简直不值一炒”。 移居美国后的张爱玲常想念苋菜拌饭,她在《谈吃与画饼充饥》中写道:“在上海我跟我母亲住的一个时期,每天到对街我舅舅家去吃饭,带一碗菜去。苋菜上市的季节,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,里面一颗肥白的蒜染成浅粉红。在天光下过界,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。” 苋菜哪里美味?相比起来颜色更诱人。一抹“苋菜红”染上半碗白饭,不用其他菜也可以吃得精光。 ▲炒苋菜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种南京地方野菜,叫芦蒿。它最能勾起人的思乡情,因为,别处没有啊。 我们同学同乡每次从外地回来,进馆子必问:“有没有芦蒿?”好像问候久别重逢的亲友一样,迫不及待来个拥抱。如果菜单上真有芦蒿,我们一桌人就会大谈乡愁:“哎呀这东西只有回来才吃得到啊!” 至于好在哪里,情怀以外,吃客都会词穷。只有汪曾祺写得妙,他说吃芦蒿,“就好像坐在了河边,闻到了新涨的春水的气味”……我们空谈味美,也说不出所以然。但你想着涨春水的生机,再看白瓷盘里芦蒿杆子配细长香干条的样子,就急切切地要扑上去。——也不用等白饭了,上饭前就把芦蒿炒香干夹个干净。吃完了,再吃饭。 ▲芦蒿炒香干(图片来自网络) 许多野菜都是叶子、芽和根茎 。但有的野菜,连草的样子都没有的,比如地衣。 地衣又称“地皮菜”,名字土,样子也土。我常去村子里“毛毛雨”家吃地皮菜,其实这种菜不得人心,因为长得不好看。它就像一个班级里真的从山沟沟里来的同学,至纯质朴,不耍一丝滑头。 有许多次客人们都吃了饭前的凉拌马兰头,尝过了荠菜汤煮鹌鹑蛋,夹了炒山芋梗子或南瓜藤,也就着香椿头炒鸡蛋大嚼一口米饭,但就是忘了红红火火青青绿绿之间的地皮菜——它灰不溜秋,又小而蜷缩着,最会被人忘记。 但我总是忘不了它,因为,它最有野菜的性格,最像一个山野里的隐形人。 ▲炒地皮菜 溧水人爱野菜,爱到两眼放光。 时下吃素流行了,上海西餐厅里一盆草都可以卖得好贵。但我们在家乡早就习惯了三餐都吃“草”——凉拌的草、清炒的草、裹馅儿的草、滚汤的草,吃不完了,还要把草晒干了或者腌起来,冬天还可以吃草…… 说起来也蛮好玩的,野菜在古代应该是饥荒必备吧?时下地位反转,进口的野菜竟然隆重打扮,和着爵士乐上了厅堂。而溧水人真是憨厚淳朴,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明明越来越稀罕的东西,却在村中挂着平实的招牌:“农家乐”。 其实噢,农家都越来越少了。物以稀为贵,以后吃野草也越来越难吧。 昨晚兴起写下这篇东西,还想写写野鸡野鸭野王八。二十年前我还会自己钓野虾,吃到家人捕猎来的野猪野兔野小鸟,也是生活的一种乐趣。 现在到处都建起高楼,人也被城市驯化了,“野”的味道自然就越来越少。 野菜看似普通隐秘,味道却真诚,很像溧水人的个性。我想这也是我爱它们的原因吧。 ▲春天雨后,石山下 李婧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caowuye.com/ksxw/1141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药象思维讲中药图文并茂的中药讲解来啦
- 下一篇文章: 国医大师朱良春痹证的辨证论治